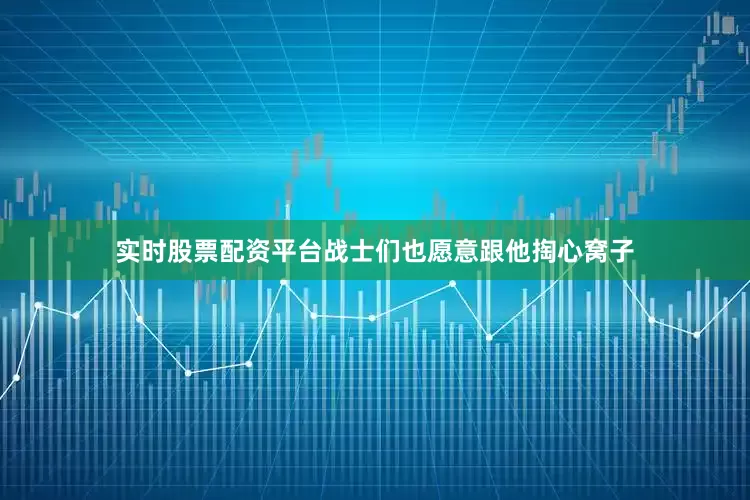
老山战场上,1987年那阵子,有个一米八的硬汉团长,听着电话里战士一声变调的“团长”,自己眼圈唰地就红了,眼泪直往下掉。你说这打仗的汉子,见惯了炮火连天,咋会因为一句话就掉眼泪?这事儿还得从那道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火墙说起。
这个团长叫刘同权,战士们都管他叫“大佛”。为啥叫这名儿?一来是他模样体型跟庙里的和佛法师有点像,看着就慈眉善目的;二来是他在战场上总干些“心软”的事儿,对战士们那叫一个疼惜,跟家里的大家长似的。但你可别以为他这“大佛”是好欺负的,人家可是有20多年党龄、27年军龄的老兵,44岁的年纪,在全集团军里都是“最老”的团长,论打仗的本事,那是实打实的硬茬。
刘同权这人,办事儿特别实在,一点不摆官架子。他常说“团长管全团,全团管团长”,从不敢把自己当特殊人物,跟普通兵一样摸爬滚打。对战士们更是上心,谁家有啥事儿,他比谁都清楚,战士们也愿意跟他掏心窝子,都信他。出征前,他跟战士们的家属拍着胸脯保证:“我跟全团同去同归,你们把丈夫交给我,我肯定给你们原封不动带回来。”这话听着简单,可在战场上,要兑现它,难如登天。
1987年5月,前线一个观察所被越军的炮火死死封了。那炮弹跟不要钱似的往下砸,形成一道火墙,后面的人冲不上去,里面的战士也撤不出来。眼瞅着观察所里断了补给,战士们三天三夜没吃没喝,刘同权急得直跺脚,赶紧给营长打电话:“把你们营部最好的东西都准备好,必须送上去!”
结果营长那边也犯了难,声音都带着颤:“团长,敌人炮火太猛了,根本上不去啊!”
刘同权没吭声,他心里跟明镜似的——要是硬下命令,让营长带人冲,说不定补给送上去了,又得搭进去几个兵。这买卖,他干不出来。可让他眼睁睁放弃观察所里的弟兄?那更不可能!一个都不能丢!
他瞅了瞅身边精明强干的作战股长,琢磨了一会儿,咬咬牙说:“作战股长上!”说着还从兜里掏出仅剩的三包烟,塞过去:“带上去,给兄弟们解解馋。”

作战股长也不含糊,仗着地形熟,左躲右闪避开敌军轰炸,还真就冲进了前沿观察所。当三天没沾着水米的战士们颤抖着拨通电话,喊出那声“团长”时,声音立马就变了调,一群大老爷们围着电话呜呜哭。电话这头,44岁的刘同权,听着那哭声,眼泪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掉——他知道,这些孩子是真扛不住了,也是真把他当亲人了。
不过有一回,他差点就没兑现对家属们的承诺。那天他在前线猫着腰观察敌情,一发炮弹“轰”的一声就落在旁边不远处,气浪直接把他掀出去老远,万幸没伤着要害,不然“同去同归”这话,就成了空话。
刘同权打炮的本事,在全军那都是出了名的,“指哪打哪”可不是吹的,命中率高得吓人。那时候咱们这边炮弹管够,可他却抠得不行,跟个老会计似的算着用。有人不解,问他为啥这么省,他板着脸说:“这些炮弹哪来的?都是老百姓一分一毛攒出来的血汗!就算再多,我也没资格随便造!”
就因为这,他定了个规矩:看见敌人,1到5个不打,凑够6个才开炮。后来前线还慢慢形成了个不成文的说法——不打老百姓、军工和女兵。不打老百姓这没说的,军人的底线在那摆着;可军工和女兵,那也是敌人的军事人员啊,她们枪里的子弹,跟男兵的一样能要命。按说对敌人心软,就是对自己人残忍,而且只要打的是敌方军事人员,上级也认可。
可真要是打了女兵,外面的说法就多了,不全是夸的。刘同权一开始不管这些,他说:“这地方,管他男女,只要是敌人,我就打!”
有一回,敌方打过来一发没装引信的炮弹,里面塞了张纸条,写着“你们太残忍了,他们都是寡妇,让你们给打死了!”战士们后来问他当时咋想的,他板着脸说“管他呢,打!”可说完又补了句“就那一回,以后再也没打过。”
谁都知道,战场上的决定哪有那么容易?很多时候,你明知道不想那么做,可形势逼着你必须做,根本没时间琢磨啥理性不理性,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

就像打345高地那回,他用了个自己琢磨的“拉网法”——先用炮火把两米多高的草丛掀开,把藏在里面的11个越军工事全露出来,排好顺序,再一门炮一门炮地逐个敲掉。一开始打得顺风顺水,可敲到七号工事时,出岔子了。
九号工事里的越军,看着一个个工事被掀翻,自己躲没处躲、藏没处藏,彻底慌了神。有个家伙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工事前,扯了件白衬衣用树枝撑着,使劲挥舞,嘴里还喊着啥。咱们前沿的指挥员都忍不住探出头看究竟。
作训股长赶紧问刘同权:“还打不打?”
刘同权没犹豫:“打!”
作训股长急了:“敌人投降了啊!”
刘同权盯着望远镜,沉声道:“5000米,我没法受降。”
这一轮炮击下来,11个敌人工事全炸了,还毁了6门迫击炮,打死28个敌人,那个摇白旗的也在里面。

这事儿后来在战士里也吵开了,大部分人都觉得团长做得对,可也有少数人嘀咕:“人家都投降了,再打有点没必要吧?”当时还有人劝刘同权,算了别打了,可他该咋打还咋打。
后来他跟大家解释:“你要是真投降,就走过来啊!现在隔着5000米摇个白旗就不打,回头这就成他们的战术了——打不过就摇旗,缓过来再接着打,咱不吃这亏!”
说实话,觉得不该打的,大多是没在前线真刀真枪拼过的,光凭着书本上的道理说事儿;觉得打得对的,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,知道那5000米外的白旗,说不定就是个陷阱。
刘同权这团长,看着像“大佛”似的慈和,可在原则上一点不含糊。他心疼战士,能把仅剩的烟送上去;他珍惜老百姓的血汗,炮弹多也不浪费;他面对敌人的“花招”,也能硬起心肠不手软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,会因为战士的哭声掉眼泪,会因为敌方一句“寡妇”的说法,后来再也不打女兵。
咱们常说“战场无温情”,可刘同权身上,偏偏藏着这么多“矛盾”的地方。你说他到底是慈还是硬?要是换作你,在5000米外看到敌人摇白旗,你会选择停火还是继续打?还有他对女兵从“照打”到“不打”的转变,是心软了,还是看透了战场更复杂的门道?
要是你身边有老兵,听过类似的战场故事,或者你对刘团长这些决定有啥不一样的看法,都来评论区聊聊。老山战场上这些真实的人和事,不该被忘了,也该让更多人知道,咱们的英雄,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符号,而是有血有肉、会疼会纠结的普通人,只是在该硬的时候,他们从不含糊!
作者声明:作品含AI生成内容
股票配资大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